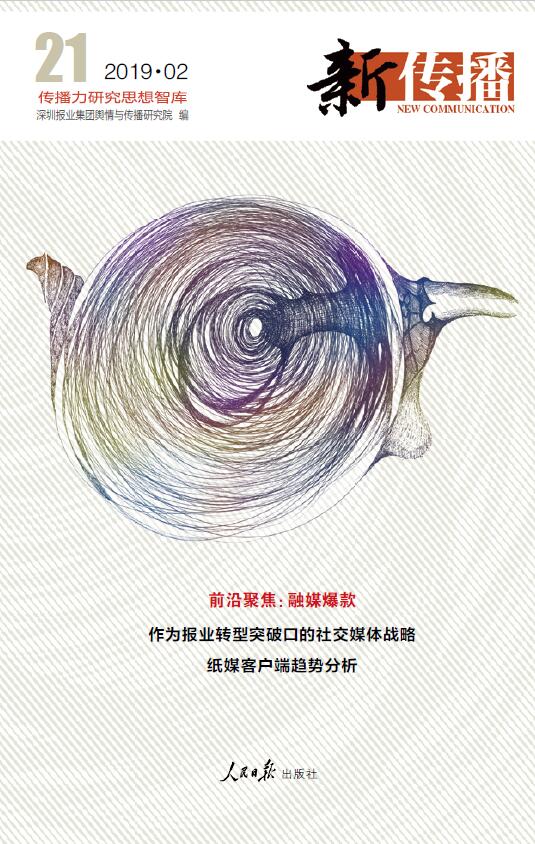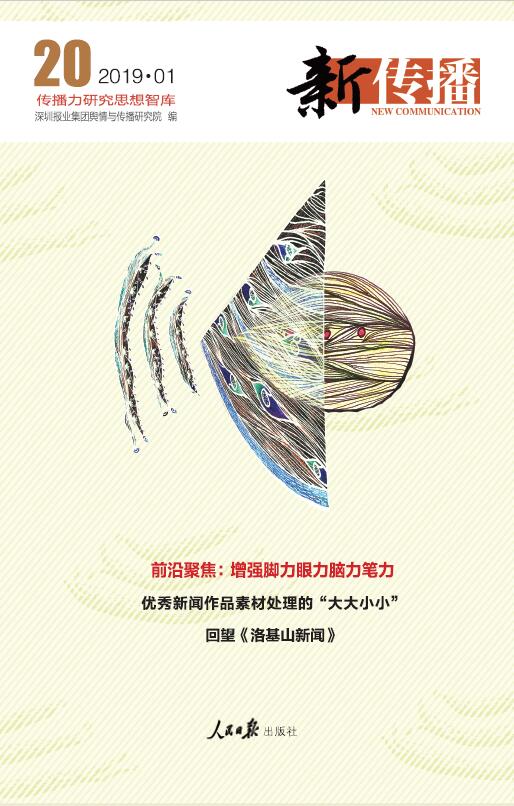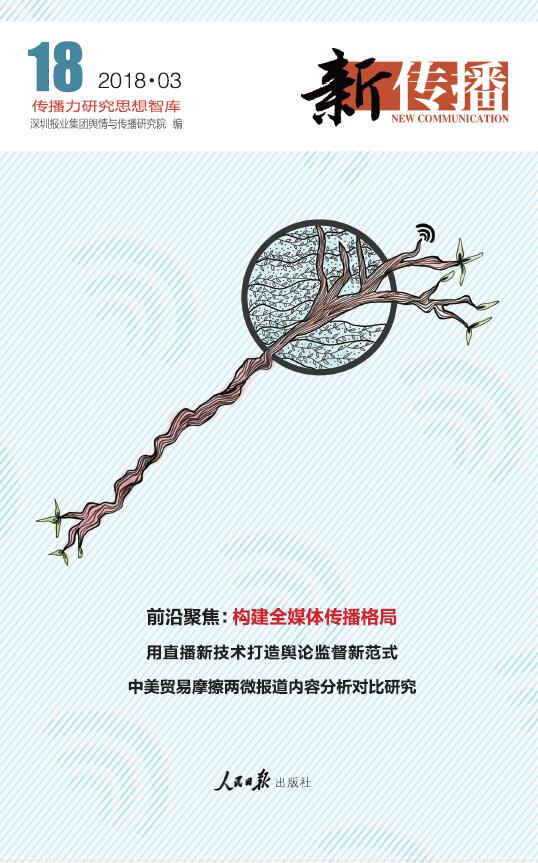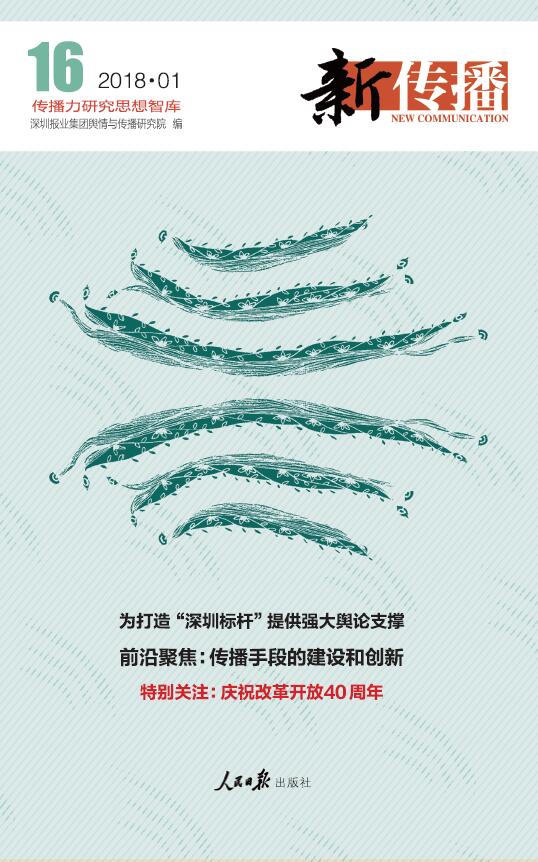十九世纪我国的对外传播及其启示意义
作者:董海涛系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文学博士 2020-03-25 17: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清朝“康乾盛世”以后,进入十九世纪的中国逐渐黯然失色,成为传统保守、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十九世纪也是我国对外传播从积极转向消极,从主动传播转向被动接受的分水岭。研究十九世纪我国的对外传播,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面临“西强我弱”的对外传播失衡局面,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自己的声音或时代强音依然不足,我们依然经常被西方媒体曲解而百口莫辩。
【关键词】对外传播 失衡 共同经验 启示
追溯历史,对外传播应当是国家产生以后并开始有对外交往活动之后的产物。类似对外传播的交流活动在中国古已有之。那时的中国被尊为“中土”甚至“天朝”,八方来觐,天下臣服。因为国力强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始终处于无法撼动的领先位置,从汉代直至前清时期,我国的对外传播基本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
因为没有大众传媒,我国早期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人际交流。2000多年前的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达。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时期非常重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两次派遣使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领数百人的驼队,穿越荒凉的沙漠,历尽艰险,用了13年的时间(经过河西走廊时张骞曾被匈奴擒获,誓死不屈,十年后才伺机逃出),踏出了漫漫丝绸之路,自此在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十多个国家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根据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ne Etiemble, 1909—2002)的描述“汉朝时期的中国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神秘而又富饶的”[1],唐朝高僧玄奘(602—664)不远万里西天取经,带回了南亚诸国的古老文化。宋朝毕昇(970—1051)发明的活字印刷,使得书籍的批量印刷和普及成为现实。及至元朝,开国皇帝成吉思汗统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成就了千秋霸业。那时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剽悍勇猛的蒙古骑兵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这些联想在许多文学作品和近年拍摄的电影《成吉思汗》中都能得到充分印证。元朝时期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17年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客观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一个物产富饶、文明发达、光辉灿烂的中国形象。到了明朝时期,西班牙探险家门多萨(Pedro de Mendoza, 1545—1618)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首次在罗马出版)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继续巩固了西方人心目中富裕强盛的中国形象。
一、十九世纪我国对外传播逐渐失衡
自明朝中叶以降,中国开始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特别是清朝“康乾盛世”以后,进入十九世纪的中国逐渐黯然失色,成为传统保守、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根据专家估计,180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GDP仍然占到世界总量的30%;而到了1900年,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到了7%。清朝乾隆时期(1735—1796),当时的大清王朝表面看起来强盛依旧,但是国家的颓败之势已经日趋显现。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学史纲》一书中对乾隆皇帝的评价极为不佳,认为乾隆好大喜功,不如其父雍正的励精图治,更不如其祖父康熙的宽厚爱人。乾隆在位中后期,清朝进入衰运。史书记载,乾隆在位60多年共六次巡视江南,前后消耗国库资金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清王朝的元气就这样被透支殆尽。乾隆五十八年8月(公元1793年8月),英国女王以为乾隆祝寿为名派遣专使乔治·马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访问中国,当年9月马葛尔尼在热河参加了乾隆83岁大寿庆典并获得接见。英国使臣先后提出了派员常驻北京,派船到浙江、宁波、天津、广东等地开展双边贸易,在京城设立商行收贮货物发卖,请拨广东省城一处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等要求。这些要求被清朝政府一概拒绝。乾隆皇帝的答复是:“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英人若贸然来华贸易,各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即时驱逐出洋。”[2]乾隆进一步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并不指望与外夷互通有无。由此可见,当时的局面还是我强西弱,清朝政府觉得自己实力强劲、地大物博且物产丰富,不愿开放通商口岸并给外国商人一定的待遇。
当时的英国已经通过数次海战胜利奠定了欧洲霸主地位,虽然对清朝的海禁制度和拒绝通商的做法也深感不满,但觉得既然是中国的定制,诉诸武力又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只能暂且忍耐一时。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东印度公司又做得风生水起。同时英国又在印度击败法国,控制了整个印度半岛。有了印度这个大本营,再向中国和周边地区扩张就显得非常便利。因此英国于1834年单方面强行将中英关系升级,派遣商务监督来华,并图谋利用坚船利炮武力占领中国。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国家形象随之一落千丈。走向衰落的东方大国当然也就成了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爆发以后,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当时马葛尔尼访问中国送给乾隆皇帝的贺寿礼物中就有世界上工艺最为先进的红衣大炮。这些大炮一直放在圆明园中,从来没有人动用或研究过它们。直到被洗劫后这些大炮才重建天日,它们锈迹斑斑,还是被尘封在原来的包装里面。”[3]
虽然钱穆先生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值得商榷,但十九世纪的确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转折时期,是我国对外传播从积极转向消极,从主动传播转向被动接受的分水岭。对外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事业的兴衰起伏与一个国家的命运跌宕紧密联系在一起。弱国没有外交,或者说弱国没有平等的外交。如果连平等的外交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国家为主体的平等对外传播。因此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看待日渐孱弱的中国便带着种族歧视和文明傲慢。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曾经对中国人有一段非常直白的描述:“他们非常贪玩,但胆小怕事;他们勤勉、恭顺,奉承起人来简直是天花乱坠。他们抱定传统的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4]
二、十九世纪两种主要对外传播力量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激烈的社会震荡和转变中,当时主要有两种致力于文化变革和对外传播的力量:其一是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为了在华传教和开拓中国市场,热衷于出版书报,在传播宗教思想和西方理念的同时,也传播西方的科技和文化知识。其二是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及部分留洋归国的学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主张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之路,兴办出版刊物,传播进步思想文化,唤起民众,推动社会变革。”[5]
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资源和地盘的战争加剧,西方国家的军队、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纷纷以各种形式来到中国,进而导致外国重要媒体和外国记者的进入。他们在我国的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如香港、澳门、上海、广州等地创办报纸和刊物。这些媒体在搜集中国信息的同时,也向自己的报社或通讯社提供中国的情况。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十九世纪外国人在我国一共创办了近300种外报和外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量的70%以上,可以说基本控制了我国的对外传播系统。在这些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中,依据不同的社会需要和读者定位,既有中文报刊如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美国传教士林乐和(Young J. Allen, 1827—1916)创办的《万国公报》等;也有英、葡、法、德、日等不同语种的外文报刊如最早的澳门葡文《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香港的《德臣报》(The China Dixon)、广州的《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新报》等。这些外文刊物大多集中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割让的城市和我国的重要通商口岸,主要为西方从事的各种活动提供思想保障和理论支持。关于外国人在华积极创办报刊之事,戈公振教授曾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总结说:从创办时间来看,葡文报刊最早,数量上则以日文报刊为多,影响势力上以英文报刊为优。外国人在我国殖民政策的努力,可以由此推而知之。
当然,因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日益悬殊,当时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覆盖面、影响力上都远远不如外国人创办的报刊。这一时期中国涉足新闻的有识之士也充分认识到报刊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清朝学者王韬(1838—1897)主张对外国报刊的歪曲报道和言论,应当“随时驳诘,以究指归”(意为即时反驳,以正视听)。他在《上方照轩军门书》一文中写道:“一宜设洋文日报以挽回欧洲之人心也。迩来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创设日报馆,其资皆出自西人。其为主笔者,类皆久居中土,稔悉内地情形,且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泰西之人,只识洋文,信其所言未确实,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为主,而中国自难与其争矣。今我自为政,备述其颠末,而曲直则自见。彼又何从以再逞其鼓簧哉?”[6]此番言之凿凿、忧国忧民的言论,从表面上看阐述了当时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的迫切需要,实质上揭示了东西方舆论话语权和主导权之争。他的超前见解不仅在那个年代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即便是在当下中国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西强我弱”的对外传播失衡局面,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自己的声音或时代强音依然不足,我们依然经常被西方媒体曲解而百口莫辩。
三、启示意义
对外传播既然因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因国家的强大而发展,那么它生来就打上了国家的政治印记,亦即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十九世纪大量的西方报刊落地中国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各种利益。在传播科学理论和社会知识的同时,这些西方报刊主要通过议程设置,有意识地宣传西方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本国政府在中国的政治传播、经济贸易和军事行动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现以一个例子加以说明,1886年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威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在《同文书会发起书》(后来改名为广学会)中公然写道:“凡欲影响这个国家的人必定要充分利用出版物。只有等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7]
此外,十九世纪由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对外传播媒体,虽然骨子里都是为西方强国服务的舆论工具,但报刊办得却并不死气沉沉,表面上也并不那么盛气凌人。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建构良好国际形象和对外传播主流价值观,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并运用“共同经验”拉近与国外受众的距离,这些做法特别值得我们的外宣媒体学习。西方媒体显然研究了当时中国受众的心理并深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道理。例如德国牧师郭士立(Karl Freidrich August Gtzlaff,1803—1851)在创办《东西洋考》这一刊物时写道:“该刊是为了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办。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让中国人充分认识我们的先进工艺、技术水平、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固有的高傲和排外意图。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必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8]为了取悦中国读者,郭士立还使用“爱汉者”(意思为热爱中国的人)作为自己的常用笔名。《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之一的威廉·米怜也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他给人写信时经常署名“愚弟米怜”,而且不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封面刊登我国儒家思想大家孔子的经典名句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多闻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等来博得中国读者的情感认同。
注释:
[1]安田朴.L’Europe Chinois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9.
[2]华文书局《清高宗实录》卷1435
[3]丁力.地缘大战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97.
[4]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化影响史述[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152.
[5] 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25.
[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1955:105.
[7]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31.
[8]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32.
编辑:何碧雯